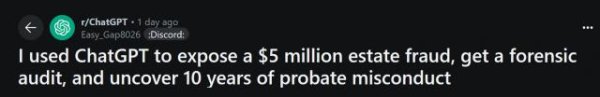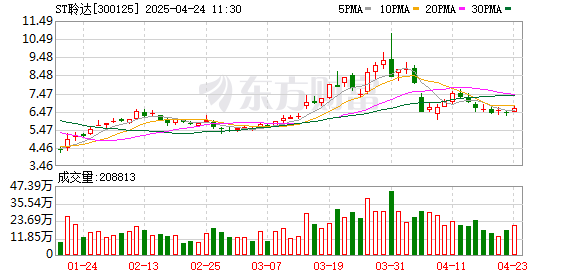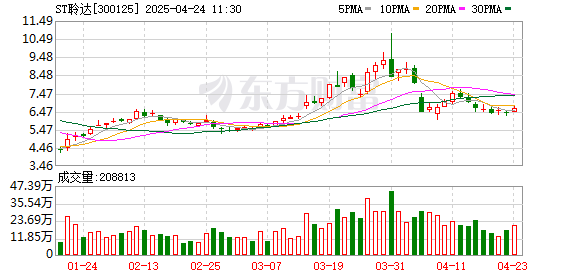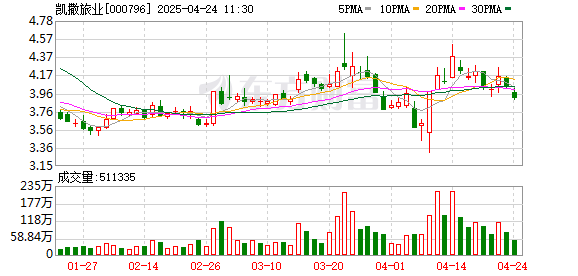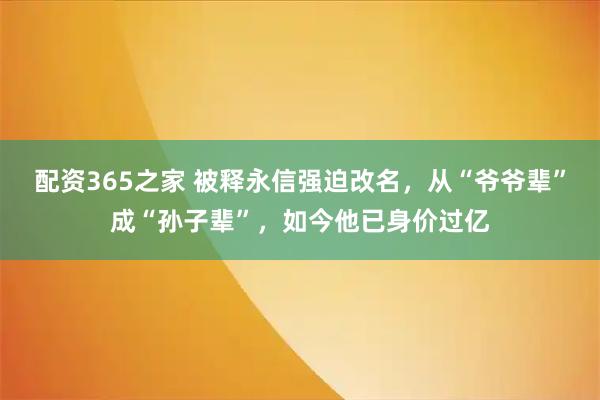因为微信推荐机制的更改配资365之家
如果您喜欢敝号
请进入敝号页面点亮“星标”
文/广成子
鲁认的日记也记载了中国大量的风土人情,其中朝鲜见不到的动植物是重点。
请输入标题 bcdef
本文欢迎转载。
朝鲜官员明朝游记专题
朝鲜见不到的物产
荔枝
在福建留居期间,鲁认见识到了不少仅在古诗文中听说的物产,抱着猎奇的心态将之一一记录在案。
例如五月初六日,鲁认正在坐营司衙门闲坐,相陪的衙客谈起近来荔枝上市,滋味正佳。鲁认自幼学诗,熟知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典故,闻此食指大动,连忙斫下一分银子凑了份子。等门子买回荔枝,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:
展开剩余90%其状大如李实,其皮红如紫泰皮。其内凝液,白如琥珀。其核如榛实而黑。其味甘滑,清液淋漓。其叶如冬柏,面差小。其结颗之状。虽数寸小小枝,多结数百介。盖此植,只在于穷方,故风尘驲骑千里来也。
对于荔枝的销售与种植情况,他也向衙客们详加询问,并一一记录。
夏节清滑珍果,莫过于此果,人人喜食,如恐未及买。市上盈积,红色遍街,一时尽卖,其利不赀。故自楚以南,家家喜植,满园皆此果。而老树数把,而最长十余丈,绿叶茂盛,红实满枝。多种村家,红绿映山。不可胜数。殖货营产者,多以此果为赖云。
生平第一次品尝到荔枝之后,鲁认便对这种南国珍果的甘滑清美念念不忘。数日后,获得徐即登资助的他又迫不及待买来荔枝过瘾。五月十八日,在参加杨洪震为其举办的送别宴上,他就着琥珀美酒饱啖一顿荔枝,随即诗兴大发,现场题了一首荔枝咏:
明珠灿烂满盘堆,珍品分明紫府来。清液爽牙消肺热,新香浃骨制龄颓。
七日后,鲁认在参加明道堂的参讲典礼时,发现例行肴果有三枚荔枝,顿时欣喜不已,风卷残云般吃掉。荔枝瘾一时没过足,又死死盯住诸位高官案前的果盘一个劲咽口水。
徐即登察觉到他炯炯的目光,当下将自己盘中的荔枝送入其袖中。巡抚金学曾见状,也命人将自己盘中的三枚一并赠予。其余诸人也纷纷效仿。鲁认满载而归,大快朵颐,颇有坡翁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雅兴。
然而所谓乐极生悲,仅仅三日之后,鲁认便觉双足刺痛,膝下浮肿,一时吓得涕泪滂沱,幸遇良医救治,方得化险为夷。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,大概率是他食用荔枝过量,导致短时间摄入大量糖分和荔枝皂苷,引起身体代谢紊乱,故而才会出现浮肿症状。
病愈后,大概是意识到一旦回朝鲜就再无机会吃到这种南国珍果,鲁认依然嗜啖荔枝如故,乃至于赠送医生的谢礼中都包括一大把鲜荔枝,实在令人啼笑皆非。
甘蔗
不知道是不是朝鲜半岛缺乏甜食,亦或者鲁认自身就嗜甜如命,他在日记中还对另一种福建的特产作物念念不忘,那就是甘蔗。
四月初八日,鲁认在从兴化府的驿道旁发现了一大片奇特田地,林差官(林震虩)告之这是粆糖草田,专门种来煮砂糖用的。鲁认试尝之下,赞不绝口。
左右长廊道傍,则皆一望无际之地。而水田之外,皆种煮草。盖煮草,乃粆糖草也。其状洽如苯草而叶青。问之则差官曰:去秋种之,今初夏真液方盛时。刈取煮之,以为粆糖。夫炼法则取液盛釜,初煮为乌糖,再炼为粆糖,三炼为冰糖云。
此草时方左右田夫刈取,故行人争借啖之。我亦借以啖之。清液淋漓。甘如生蜜。
林震虩所说的“粆糖草”,其实就是甘蔗。甘蔗原产印度半岛,早在先秦就传入中国南方,至迟至西汉已见相关记载。
福建正是我国甘蔗制糖的发源地之一。宋苏颂《图经本草》云:“甘蔗……可榨汁为沙糖,泉、福、吉、广诸州多作之”。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也曾提到泉州大量生产和销售食糖。
明代中后期,随着砂糖贸易兴起,甘蔗的种植在八闽大地上更见流行。史载福建一省“货之属皆有糖,果之属皆有蔗”。陈懋仁《泉南杂志》载:“甘蔗,干小而长,居民磨以煮糖,泛海售焉。其地为稻利薄,蔗利甚厚,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”。
巨大的利益驱动下,自古善于营商的福建人“家家种蔗,户户煮糖”,于晚明形成了“无日不走分水岭,下吴越如流水”的蔗糖贸易盛况。《锦溪日记》对此的记载恰为佐证。
双季稻
除了甘蔗之外,鲁认在日记中还记下了另一种令他困惑的农业现象。
左右水田处,禾穗将半秀出。怪而问之。差官曰:地虽南尽。风气早热。四月念间落种,五月收获。而五月再种苗,十月又收获。一年之收,禾实倍出云。
当日刚刚四月初九,鲁认却发现水田中禾穗已经半吐,而按照农业规律,这个时令理稻谷应刚刚由苗成穗才对,大大有违常理。林震虩解释道:“福建地处南国,气候偏暖,因此成熟较早。四月间(农历)播种,五月底(农历)就能收获。然后五月(农历)再插秧苗,十月(农历)又能收获一次。一年收获两次,稻谷产量双倍,俗称双季稻。”
鲁认所看到的正是“双季稻”,又称“再生稻”。顾名思义,双季稻即一年中双收双造。通常于五月中下旬(阳历)播种早稻秧,七月中下旬(阳历)收获,称为早稻;收获完早稻后立即翻耕水田,赶在立秋前插种晚稻秧,至十一月成熟,赶在降霜前完成收割,称为晚稻。
据地方志文献《仙溪志》载:“稻,种类非一,有一岁两收者,春种夏熟曰早谷,《闽中记》谓之献台。既获再插,至十月熟,曰禾庶。有夏种秋熟,曰晚稻,无芒而粒细曰占城稻。”至晚从南宋开始,中国南方即有栽种双季稻的记载,而福建正是此类稻种适生区域的北界。
进入明代后,海洋贸易蓬勃发展,闽人开始大量改种甘蔗等经济作物,这就导致福建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之地出现了粮食危机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闽人开始大力推广双季稻,遂在明代中后期形成了“闽中之田,几半种再熟稻”的局面。《锦溪日记》的相关描写正是上述历史情形的生动注脚。
至六月二十二日,鲁认登城远眺,果然看见郊外早稻已经收割完毕,农夫正在插莳晚稻秧苗。一切皆如林震虩此前所言。
晴。与曾秀才登城观望,则郊外早稻尽已收获,而又即反耕种苗。怪而问之。秀才曰:南方极热。正月落种,五月收获。而五月种苗,十月收获。一年再种而再收矣。
南国名花
除农作物外,《锦溪日记》还记载了两种稀有的闽地花卉。鲁认与明朝友人就此进行了一番友好的文化交流,姑且录写于下。
其一是在呼总兵(呼鹤来)衙门里所见的蜀茶花。
阶上盆中,有一条春柏盛开。呼将军曰:此花贵国亦有否?答曰:我国多有,而其种有二焉。一种则严寒雪中盛开,故名曰冬柏花。而又一种则春风始开,故名曰春柏矣。将军曰:此花果是柏种,然中华则通称曰蜀茶花。盖蜀人,摘以嫩叶为茶,故名之也。
其二为鲁认在黄秀才(黄虑阳)房中作客时玩赏的石榴花。
黄秀才房外有小池。墙外有石榴花。秀才曰:贵国亦有是花否?。答曰有之。秀才曰:此花之名,亦知所自来乎?答曰不知。秀才曰:此种初自安石国荐入,故因名曰石榴。盖此花最晩,独开于五月无花之节。其中则明珠满腹,清液酸甘,治养脾胃。江北则无之,江南则有之。若达江北则其直倍于黄橘,故南人善种。我答曰:盖此花,我国亦多有之。而艳花美实,且助骚人吟咏之兴。故古人曾有五月榴花照眼明之句。
珍禽异兽
留居福建期间,鲁认也曾亲眼看到了一些中国特有的动物,并将其当成异闻特意载入日记。这些动物于明朝人眼中本属寻常,可在异国远客眼中,却不啻为珍禽异兽。
比如他在坐营司休养期间,曾有幸看到了古书中记载的孔雀,不由得啧啧称奇,将其形貌、食性和产地记录在案。
有一人笼孔雀来,献坐营司。坐营喜而赏银一两,即开笼放于庭中。翠羽丹顶,饮啄如鸡,最喜白饭。我问之衙客曰:此鸟何国之鸟也?客曰:产自西域,入于中国,而孔子家养,故曰孔雀。自此之后,家家喜养。
笔者按,鲁认对孔雀名称由来的记载有误,那位衙客的解释显然属于望文生义。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孔,通也,亦嘉美也。”此处的孔字在孔雀一词中宜取其嘉美之义。鲁认虽然博闻强记,在这一点上也不免犯了格物不谨的毛病。
而在另一种动物的认知上,鲁认同样有所偏差。四月二十二日,登临平远台远眺之际,他望见下方的草场上有一大群黑乎乎的牲口。
一行见场亩四边黑角牛数百,成群龁草。我问此牛:乃海中所产水牛云然耶?同行衙客曰:岂是海中之产也,本是村家耕田之牛。但南方至炎,五六月间,则喜卧水中避暑,故名之曰水牛矣。盖其状,腹大臀广,毛色全黑,倍大于凡牛矣。
堂堂朝鲜官员,居然连水牛都没见过,还以为是海中所产的怪兽,实在匪夷所思。不过话说回来,历史上朝鲜素以弓矢精良著称,凡制良弓非水牛角莫办,鲁认又何以连水牛都没见过?这里就牵扯到历史上的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一段往事了。
简单说来,其实朝鲜半岛最早是有水牛的。考古发现,半岛北部的黑隅里遗址就出土过若干大型水牛角,属于一种古代的东北亚野水牛。这类野水牛曾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,但在中古时期趋于灭绝,自此朝鲜半岛所需的水牛角开始依赖进口。
针对这一弱点,明、清两朝都曾将水牛角当成战略物资加以管控,严禁私输朝鲜境内,有时甚至会在贡品货单上强索此物,意在削弱半岛政权的军备。
到了鲁认生活的十六世纪末,东北亚野水牛在朝鲜半岛早已销声匿迹,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水牛角制品在朝鲜广泛使用,却几乎没有人见过活体水牛的缘由。
综上所述配资365之家,鲁认以“猎奇”心态记录的闽地风物,实则是一部晚明福建生态、经济与文化的微观史,也是东亚物质文明交流的生动脚注。
发布于:北京市华夏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